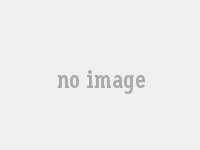宗月,小羊圈,和傅高义
小羊圈图,老舍1947年画的。
一个
1950年2月15日,一个中等身材的房客走出王府井西路以北的北京饭店。他很胖,走起路来脚步沉重,身体都是歪的。他的服装和其他***不相同:他的毛皮大衣外面套着一套西装,但他穿着两条带裤腿的蓝色丝绸棉裤。他看起来怪怪的,怕冷,似乎不适应12月的天气——冷得好像连空气都冻住了。
这个看过去特别的新人不是别人,正是年前从美国回来的老舍。
12月11日,他坐上了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他一出前门车站,就看到了前来接站的楼世一。他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昌相遇的老朋友。老舍随他来到王府井,住在这座早年法国人修建的七层洋房里。然后,他让老同学帮他四处看看,想买个三合一的小院子。
为了筹集资金,他还写信到美国,要求代理***卫·劳埃德从纽约寄来版税。他说:“我家在从重庆回来的路上。我得给他们买个房子。现在,北京又成了首都,在这里找一套心仪的房子既贵又麻烦。如果你能寄500美元到香港,我将非常高兴,这将由侯博士转交给我。(香港香港大学病理学系侯宝璋博士)
因为没有一定的工作要参加,除了开会、接待访客、走亲访友,他就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或者靠在沙发上看解放区的文艺新书,或者就在梳妆台前躺着照一面大镜子。
他以招待所为家,在宾馆二楼222房间住了两个多月。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只能整天呆在酒店楼上。在美国,他的腿生病了,走路很困难。拄着拐杖,勉强走到酒店门口,出了门还要坐车。他抱怨道:“我真的很喜欢吃一些烧饼。但是,我离开餐厅走到东单,也就是普通人三分钟的路程,却要走半天,休息四五次!"
不过,他今天无论如何还是要去一趟。他要去东安市场从内地银行取5万元。他必须在新年前拜访珍妮宗悦并给她压岁钱。过了明天,就是大年初一。
二
这些年来,老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但他在北平的至亲好友始终在他心里。
回京,-北平两个多月前改打电话回京,得知许多亲人平安,尤其是珍妮宗悦还活着。他真的很激动,很欣慰,也有点难过。——恩人宗悦成为大师已经八年多了。
宗悦和老舍一样,也是满族人。他是西北城里有名的“好人”,乐善好施,帮助孤儿和穷人。在出家之前,老舍称他为“刘叔叔”——那时他的名字是。后来老舍到了上学年龄,应该是去跟八岁的弟弟当学徒了,而不是去读书了。由于刘叔叔的帮助,她很幸运地进入了私立学校,不用交学费和书本。
而龙,他听说这两个家族的来历,更是深远:
“他和我们的关系相当有趣。虽然我曾祖母帮过他家,但我们不是他的奴隶。他的爷爷和爸爸,还有我的爷爷和爸爸,总是有关系的,不过关系不大。直到他成家,这种关系一直没有断过。”
字里行间,他们是世交——四代人的友谊始于曾祖父那一代。他还记得,老年人之间的事情,老一辈人说闲话的时候,常常要说:
“我的曾祖母跟随一个满族官员到了云南等遥远的地方。官方拿到多少元宝是毋庸置疑的。我曾祖母的任务大概就是帮官人的老婆上、下轿子,给她包烟、倒茶。在我们家,我们不提曾祖母的这些任务,只记得是她买了我们的房子。”
曾祖母的传说正好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爷爷奶奶属于正红旗,而他出生的时候却生活在正黄旗的土地上。
按说当年清朝入关建都的时候,老舍打过仗,被分到西直门军营里的住房。大概在他曾祖父那一代之前,他家就没落了。“北城外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辈卖了,只剩下一亩,衬着几座坟墓。分配给他的房子也是祖上卖的,换成烤鸭吃,他不得不考虑找房子搬家。也是在这个时候前后,朝廷的八旗禁令逐渐放松,贫困的旗手有了行动的自由。于是,当外放放大镜任期结束回京时,随行的老舍的曾祖母,用帮佣工人的收入,在靠近护国寺西墙的一个小羊圈里,盖起了房子,一家人搬出了红旗。
老舍出生在一个小羊圈,但不得不说,这也有赖于宗悦祖上的荫庇。
三
羊圈是老舍的出生地,《四世同堂》和他的自传体小说《红旗下》中的大部分事件也发生在那里。
老舍湖沉没后的第十三年,胡介卿和亦舒母子比较好次来到小羊圈,也就是现在的小杨家胡同,画了一幅小说《四世同堂》中的小羊圈胡同的草图。然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老舍在1947年初春还画了一幅小羊圈的地图。
老舍手里画的地图比他家画的地图还要精确。这是一幅惟妙惟肖的“葫芦图”,但葫芦不是坐着的,而是平躺着的:它的嘴朝着西街,屁股撅着朝东。画面是用钢笔在一张A4大小的普通书写纸上画的,用英文清楚地标注着“小羊圈”、“街道”、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一至七号院落的分布,以及两棵大树的具体位置。注意看图,用笔简单恰当,一眼就能看出来;与《四世同堂》中的描述相比,***没有出入:
“也许,这个地方一开始真的是羊圈,因为它不像北平的普通胡同那样笔直,或者略带一两个弯,而是像个葫芦。通向西街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长,很脏。葫芦嘴特别窄,如果不仔细看或者不去问邮递员,人们很容易忽略过去。进了葫芦的脖子,看到墙边堆积的***才敢往里走,就像哥伦布看到海上有东西漂浮才敢往前走一样。走了几十步,突然看到葫芦胸:一个东西有四十步,南北三十步一个圈,中间两棵大槐树,周围六七户人家。再往前走,还有一条巷子——葫芦腰。穿过‘腰’,还有一块地空,比‘胸’大两三倍,这就是葫芦肚。”胸”和“肚”大概是羊圈吧?”
老舍写了羊圈的方位,并手写解释了祁家的由来:
“祁家就在葫芦柜里。街道朝西,对着一棵大槐树。当初齐师傅买房,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要得到”。
老人齐是四世同堂的祖父,也就是曾祖父;他们是十口之家。小羊圈里老舍家的房子是她曾祖母买的,刚好住了四代。
世界上有什么巧合?
四
老舍的《羊圈图》是给溥爱德画的,供她翻译参考。
我抄了蒲副官1978年10月20日写给夫人杨的半封信。那年夏天,老舍没有骨灰的骨灰盒被隆重地安放在八宝山。普埃德听到这个消息,写信给戴乃迭,说:
“1946年和1947年的冬末春初,我和他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他用英文把书名翻译成了《叶露风暴》。他每天晚上七点钟过来,我们一直工作到十点钟。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我要在美国帮扶中华总工会***会的办公室工作,要忙一整天才能收工(还好当时不用去外地活动)。”
在同一封信中,蒲艾德还说:“我们的工作方式很不寻常。老舍用中文朗读,我用英文打出来。他对英语的实际掌握程度比他所说的要高。我一边打字一边读给他听。他经常提问,会帮我纠正。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难的地方。我记得,他特别喜欢我把‘瓜头花子’翻译成‘为首乞丐的工贼’。”
五
溥爱德的信,老舍的羊圈地图,四世同堂的译本,都是七八年前的一个暑假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找到的。
那年7月我到美国后,比较好站是纽黑文。我计划在耶鲁大学上一周的课,然后绕道罗德岛,去傅高义教授位于波士顿附近剑桥萨姆纳街14号的公寓,先讨论并出版他的日文,然后去他家西边不远的施莱辛格图书馆,查看保存在那里的普艾德档案。
去年5月下旬的纽约,就在身着浅蓝色长袍的哥大本科生在白色帐篷下高高兴兴举行毕业典礼的这两天,我在巴特勒图书馆善本和手稿部找到了老舍和溥爱德签署的翻译合同,得知一家四代人的英译本在哈佛大学仍保存完好:溥爱德于1985年去世,享年96岁,许多档案捐赠给了施莱辛格图书馆。它是美国比较好个女性研究的专业图书馆,以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亚瑟·麦·施莱辛格教授命名,他的儿子小施莱辛格是费正清的妹夫,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其所在的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原本是美国***的女子学校。
这是一个典型的神秘的新英格兰夏日午后。天气很热,一丝风也没有。极高的蓝天上,飘着厚厚的白云,一朵朵,一动不动。因为是假期,偌大的图书馆里看不到几个人,尤其是二楼明亮的阅览室。近30箱蒲爱的档案一一送来后,我很快找出了老舍画的羊圈地图,蒲爱的一些书信,以及她翻译的一屋之下四代人的全部手稿。人们一直以为这部写于70多年前的长篇巨著是没有希望看到全貌的:1950年5月13日,老舍将定稿的《饥荒》前十章送到《上海小说月报》发表。跑了不到一年,就无病而死。15年后,八月下旬的一个血淋淋的日子,老舍闯进了一大群少年,《饥荒》未发表的手稿,在富人胡同19号的院子里,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下午的一半,我从图书馆出来,来到傅高义教授家,谈出书的事,然后谈档案馆里的《四世同堂》译本,还有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的横山勇三教授写的一封与他有关的信。——横山是青木昌子的弟子,1973年11月赴哈佛做访问学者。老舍的美国经历是他的研究课题。
在衡山的信中,他问了许多至今无人能回答的问题:
[1]老舍是什么时候应***邀请来美国的?你一个人来的吗?如果有,他访美期间家人在哪里?他一个人住在美国吗?
[2]他来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3]他来的时候病得重吗?你被治愈了吗?
[4]他住在美国的什么地方?
[5]据说他在纽约写了一篇长文。如果是真的,它说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写,什么时候写完?你还写过其他作品吗?
[6]除了写作,他还做了什么?
[7]他觉得这里的生活怎么样?
[8]他什么时候离开美国的?
[9]他为什么回红色中华而不是台湾省?如果他没说,你觉得他的理由是什么?
[10]他回到红色中华,***怎么说?
衡山在信中还说,由于没有老舍的资料,他通过傅高义教授联系了威尔玛。她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文化关系官员。老舍和曹禺访美都是由她具体安排的。但由于美国***档案的缺陷,她无法提供更多信息,而是向他推荐了普艾德。
“是这样吗?”傅高义先生笑着说:“我印象中他是哈佛来的,但我不知道这封信。”
后来我抄了衡山的信,寄给了老舍研究道路上衡山最重要的引路人傅高义先生。他当时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
四十年后,傅高义先生作为向导在同一条路上出现在我面前。四年前的八月,由于他的无私帮助,我得以在费正清***研究中心工作。
六
在哈佛的那一年,我们住得离傅高义先生很近,就在街对面。
我们住的房子,门牌号是欧文街109号,位于神学院旁边一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中间隔着一条不宽的小路,朝北的黄色建筑是东亚系的办公室,***留学生经常三三两两地进出。斜对面的东北角有一棵高大参天的老树,美国文理学院的房子隐藏在密林深处。
傅高义先生也认识我们的房东安德鲁和他的母亲玛丽安。这位老太太是小教授亚瑟·麦·施莱辛格的遗孀,她的姐姐是威尔玛,两人都出生在拉德克利夫。
比较好次见到玛丽安的时候,我谈到了我正在研究的老舍。104岁的她重听,激动地大喊:
“老金?!你也认识老金吗?我认识他!”
八十二年前的夏天,二十三岁的玛丽安独自一人乘船从三藩市经上海到北平见费正清和威玛,于是与梁思成、林、金等成为挚友。
近年来,每当我谈起傅高义先生,我就会想起他给我的研究和对我们家庭的关怀。他的笑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此时,老舍纪念宗越大师的一句话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没有他,我可能永远也不会上学。没有他,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记得帮助别人的乐趣和意义。”
老舍的话,尤其是后一句,也是回忆傅高义先生的时刻,我心里最想说的话,——我不敢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但是已经伤害了人们三年的文君仍然拒绝停止伤害。
往年元旦,凌晨1点半,打浦桥。
吴平
【纠错】推荐文档
- 11.安徽建筑工程学院,安徽建筑工程学院是几本
- 12.动物科学专业;动物科学专业考公务员考什么职位
- 13.养老金入市;养老金入市***消息
- 14.童话世界里的奇妙冒险
- 15.天津快板台词—天津快板台词短的
- 16.广东科技技术职业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代码
- 17.大连理工学院;大连理工学院盘锦校区
- 18.南京工程学院,南京工程学院录取分数线预测(数据为往年仅供参考)预测2023
- 19.小学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出来当什么老师
- 20.夫子庙小学;夫子庙小学学区
- 21.奥鹏学生登陆(奥鹏学生登录平台登录不了)
- 22.新乡医学院教务处-新乡医学院教务处网络管理系统
- 23.保定市中考成绩查询—保定中考成绩查询入口2021
- 24.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介绍)
- 25.华天学院-华天学院厦门子宫
- 26.上海房地产开发公司;上海房地产开发公司老板
- 27.兴趣爱好特长;个人兴趣爱好特长
- 28.卡塞尔大学、卡塞尔大学什么档次
- 29.山西高考录取查询—山西高考录取查询步骤
- 30.沈阳工程学院地址—沈阳工程学院地址英文
- 31.广州武警指挥学院、广州武警指挥学院黄峰
- 32.河南洛阳理工学院—河南洛阳理工学院录取分数线预测(数据为往年仅供参考)预测
- 33.梦见人民币、梦见人民币都是一捆一捆的
- 34.对外经贸大学自主招生、对外经贸大学招生办
- 35.广东省计划生育政策(广东省计划生育政策文件)
- 36.东北农业大学录取查询-东北农业大学录取结果查询
- 37.河北会考成绩查询网-河北会考成绩查询网站入口2020
- 38.天津外国语大学分数线预测(数据为往年仅供参考)预测-天津外国语大学分数线预测(数据为往年仅供参考)预测是多少
- 39.bdschool(bdschoolppq是什么意思)
- 40.保定高等专科学校,保定高等专科学校有哪些
- 41.焦作工贸职业学院—焦作工贸职业学院官网
- 42.宁波城市职业学院_宁波城市职业学院是公办吗
- 43.江西高考网(江西高考网官网登录网址)
- 44.河北外国语学院—河北外国语学院专业有哪些
- 45.梦见小女孩;梦见小女孩掉水里了是什么意思
- 46.2013年消防日主题(往年消防日的活动主题是什么)
- 47.qq个性留言—qq个性留言大全
- 48.长春市人才-长春市人才档案中心
- 49.温州肯恩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学费
- 50.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 51.江苏科技大学分数线预测(数据为往年仅供参考)预测—张家港江苏科技大学分数线预测(数据为往年仅供参考)预测
- 52.三句半搞笑台词;经典三句半台词大全爆笑
- 53.江西文科状元、江西文科状元张弘毅
- 54.指导意见_指导意见有没有法律效力
- 5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 56.黄骅新世纪中学、黄骅新世纪中学宿舍图片
- 57.节约用电标语—节约用电标语幽默风趣
- 58.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2023
- 59.适合公司年会歌曲;适合公司年会歌曲大全
- 60.爱情短语;爱情短语5到7个字
- 51.内江泰来职业学校学费
- 52.一级造价师哪个专业好考
- 53.ABCB式的成语大全
- 54.团队拓展游戏心得4篇
- 55.孙子满月宴贺词
- 56.高二语文得分技巧
- 57.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哪些专业?
- 58.国内少儿编程培训机构报个班需要多少钱
- 59.中级摄影师考什么
- 60.《岁月神偷》观后感
- 61.2023年内江财经会计专业职业学校哪所好
- 62.2023广元市交通技工学校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是多少(附要求、条件、对象)
- 63.南充电子工业学校航空服务专业课程设置有哪些
- 64.四川信息汽车职业技术学院雪峰校区学费
- 65.千万别来沈阳化工大学?为什么都不建议上沈阳化工大学呢?
- 66.四川卫生学校的招生要求怎么样?
- 67.***五冶大学怎么样?
- 68.四川往年初中生上汽修学校好吗
- 69.「成都龙泉驿区汽修学校有哪些」成都龙泉驿区汽修专业哪个学校好
- 70.四川国盛技工学校开设有哪些专业?计算机网络应用专业好学吗